来源:发布者:时间:2022-12-03
□记者 孙芸苓
11月20日晚,由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委宣传部、湖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北京中央歌剧院拉开帷幕。35位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齐聚一堂,在隆重典雅的颁奖礼上接受中国文学最高荣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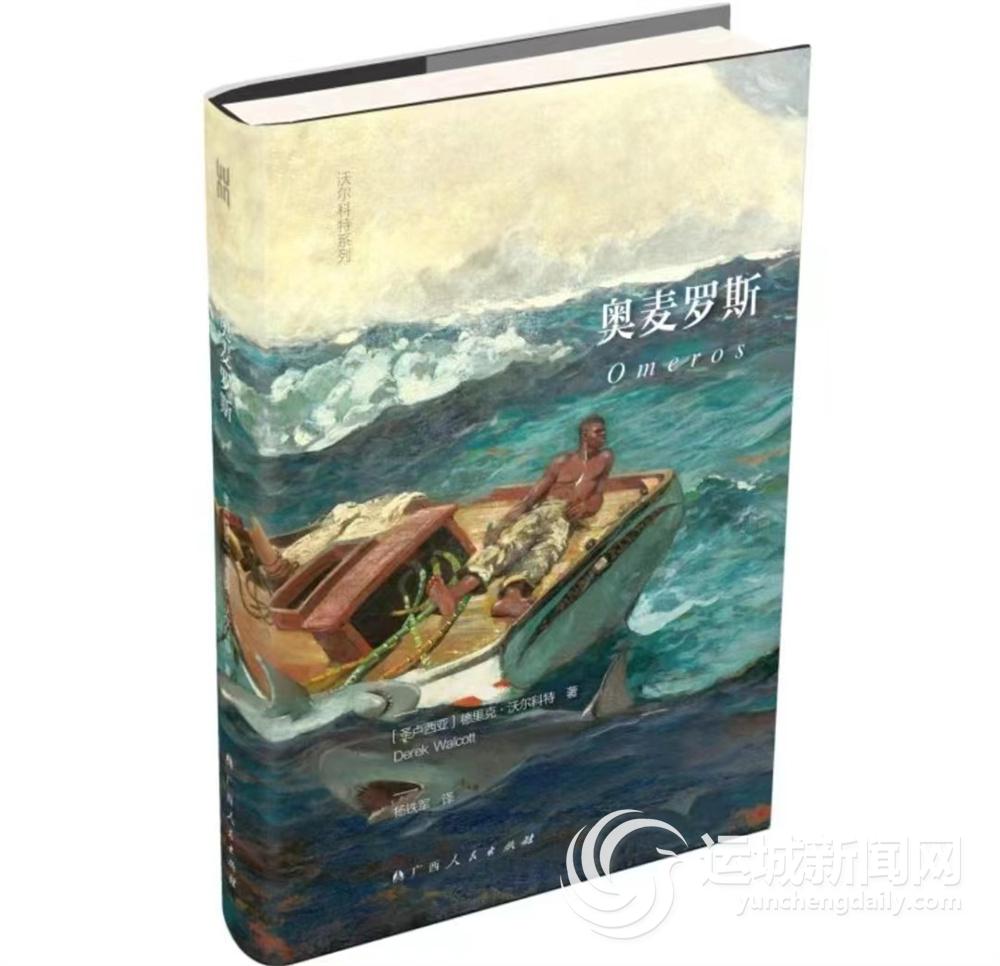
杨铁军译《奥麦罗斯》书影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共评出5部优秀译著:许小凡译《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杨铁军译《奥麦罗斯》、陈方译《我的孩子们》、竺祖慈译《小说周边》、薛庆国译《风的作品之目录》。
当晚,获奖作品《奥麦罗斯》的译者杨铁军,代表翻译奖获奖者在“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颁奖礼上发表了感言。
在感言中,他问自己也问同行:“每位译者都可能面对过这样的问题,诗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推而广之,文学性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但如果文学翻译注定失去文学性,那么译者何为?”
这个问题,杨铁军是有答案的,他说他更愿意从肯定性的层面来理解这个否定性的问题:“文学翻译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其本身便蕴含了一个最根本的人生伦理。也就是说,在承认不完美的前提下创造完美。”
杨铁军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位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过比较文学博士、后来又退学考取计算机硕士的海归,主要翻译的是诗歌。主要翻译作品除了沃尔科特(圣卢西亚)的《奥麦罗斯》,还有弗罗斯特(美国)的《林间空地》、希尼(爱尔兰)的《电灯光》、佩索阿(葡萄牙)《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等。
最后,英语文学翻译家、诗人杨铁军衷心希望每位译者都能在为了“不可为”而“为之”的旅途中耐心跋涉。
得知杨铁军参加完颁奖仪式回到芮城,记者用微信联系上他,约好前去采访。不料因为静默我们无法见面,只能在微信上提了几个问题和他沟通。
杨铁军是芮城人,198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95年,他获得北大世界文学硕士学位,赴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后从事软件咨询开发工作。
多年的积累,令杨铁军收获颇丰。他翻译的《奥麦罗斯》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实至名归。
如今,他定居家乡芮城,一边陪伴老人,一边写诗、译诗。他表示,今后将继续为中国读者带来更多优秀的西方诗歌作品。他最新翻译的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的《生活研究暨致联邦死者》已经交稿,正等待面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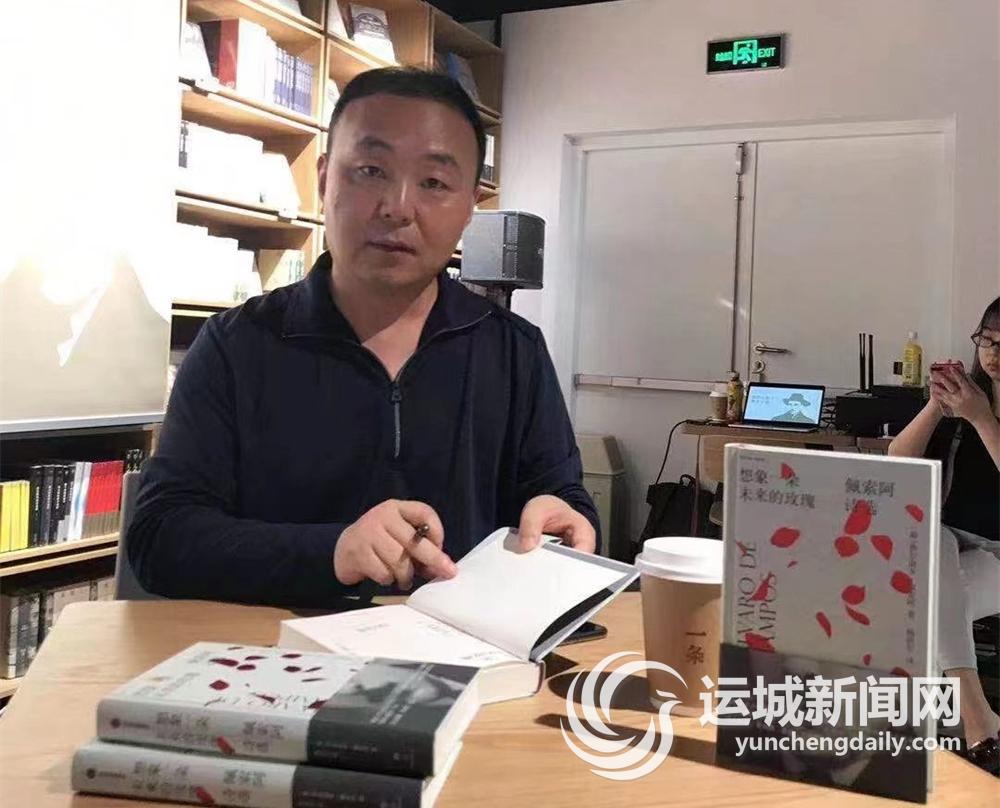
杨铁军近影
记者:杨老师您好,首先恭贺您荣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是怎样一个契机让您决定翻译《奥麦罗斯》这样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歌作品?这样一个大部头,对翻译者是一种考验。
杨铁军:《奥麦罗斯》在被中国读者了解之前,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也许因为了解不够,所以很多人甚至对它有一种敬畏。
当时编辑找到我商谈翻译这个大部头时,我也有些畏难的情绪,但我这个人愿意挑战自己,于是接了这个任务。
我翻译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标准,就是是否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我的初衷就是在汉语中呈现我对原作的理解,这个理解必须配得上原作。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必须反复琢磨、下够功夫,下多少功夫,就有多少收获。从翻译《奥麦罗斯》的经验中,我深切体会到这点。
记者:在翻译《奥麦罗斯》的过程中,作为一名诗人,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杨铁军:《奥麦罗斯》在西方被认为是一部有后殖民主义色彩的作品。这部作品意图在加勒比海的“本地”和西方中心的“别处”求得某种形式的和解,这虽然不是一种最典型的后殖民主义主张,但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学实践和思考。
《奥麦罗斯》的艺术价值也是其在西方得到好评的原因。在中国,这几乎是唯一的原因。
我认为《奥麦罗斯》完全配得上中国文学界对它的推崇。
沃尔科特对加勒比海地区在后殖民时期的命运和前途的思考,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我们亦需思考,如何与西方文化形成一种健康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对其盲目服膺或排斥。
记者:《奥麦罗斯》在创作手法、情感抒发上,对中国诗歌文学创作有哪些启发?
杨铁军:《奥麦罗斯》从文学上看代表了一个巨大的“野心”,而且是被实现的“野心”。英国诗人艾略特所著长诗《荒原》统治诗坛后,长诗、史诗这个体裁被整个颠覆了。有观点认为长诗已死。还在继续写长诗的人,都在暗暗与艾略特较劲,往往选择更激进的形式。
但大部分长诗实践都难说成功。
在“后艾略特时代”,《奥麦罗斯》创造了一种表面上似乎在回归传统,实际上却是很现代的手法。把传统和后现代、后殖民等矛盾的认识融合在一起,不仅做到了形式上的解决,也达到了文化认识层面的和解。这应该算是一条有参考意义的道路选择。
沃尔科特是一位明喻大师,《奥麦罗斯》这么长的一首诗,自始至终都能保持明喻的高难度腾跃,技巧实在高超,让人不由忘记了诗歌写作的各种忌讳,从而体验到最大限度的自由。这都是中国的写作者可以学习的东西。
记者:我发现您的求学经历里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您在美国读比较文学博士的时候转向了计算机专业,是什么原因让您做出这么大跨度的转变?
杨铁军:那时候我在爱荷华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已经读了4年,课程基本都已修完,就差毕业论文了,但我对自己所学的东西越来越感到厌烦。4年里所学的大量理论,包括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解构主义、人类学等,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不存在文学性。文学研究关心的是文本所反映的具体历史境况下的权力关系。既然文学性不存在,那么写诗有什么意义呢?只是给理论提供剖析的文本?那做广告,甚至写小纸条岂不是更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出国四五年,几乎没写什么诗,觉得自己陷入了极度的焦虑。对我最重要的始终是写作。
自从我开始写诗以来,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写作进行的,我想象不出不写作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既然写作遇到了麻烦,那么肯定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理所当然”地把问题归咎于与写作相互冲突的那些文学理论。
记者:您当年是咱运城的高考文科状元,先是学习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后来又轻松跨入计算机行业。这两个专业好似分列文理科两极,一端是感性思维,另一端则需要极强的理性思维,您怎么协调这两种思维的差异?
杨铁军:我之所以不学比较文学,就是觉得我所学的东西和我的写作之间,有解决不了的矛盾。改行计算机后,很快就恢复了写作,也许并不是巧合。写作状态好的时候,往往也是工作效率高的时候。所以,我并没有强烈地感觉到两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至少对我来说,基本都是想象中的。
记者:随着您的获奖,您的家乡芮城也被更多人所知。我知道您也是诗人,谈谈您对故乡的印象和您诗歌里的乡愁。
杨铁军:我对家乡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小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认知,因为自己生活在其中,也没有自觉意识,唯一知道的是站在悬崖上,可以看到下面的黄河,抬起头,可以看到另一边的中条山。还有一个记忆就是小学课本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以及“坎坎伐檀兮”,下面的注释说是芮城民歌。
后来离开了家乡,很多年之后,才有一个回头看的意识。才意识到家乡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最重要的是,意识到作为一个诗人,家乡对自己的意义。我有意识地写了一些关于家乡的诗,希望能够更深切地了解这片土地,给自己的写作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记者:您能给故乡的文学爱好者一些建议吗,如何在文学创作作品中尤其是诗歌创作中突破自己及地域的限制,写出更优秀的作品。
杨铁军:我可能并没有资格给扎根于河东大地上的写作者什么建议,因为能够扎根在这块土地上是一种巨大的优势。沃尔科特说,一个诗人有效的处理范围是方圆二十英里。只要能把握自己和周边的人和事的关系,就已经足够了。
当然,一个写作者必须有宽广的世界意识,在现今资讯发达的时代,这都是能够通过大量的阅读来培育的。还有一个我经常和朋友说的一个原则是,“破除迷信”。有很多关于什么是诗,什么是好的写作的说法,但这些说法说到底都是历史经验,虽然可能都是正确的,但并不代表您的写作可以因循守旧,必须有打破这些教条的勇气,才能确立自己对于诗的定义。
运城日报、运城晚报所有自采新闻(含图片)独家授权运城新闻网发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例:“运城新闻网-运城日报 ”。
凡本网未注明“发布者:运城新闻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