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运城晚报发布者:时间:2023-07-13
□衣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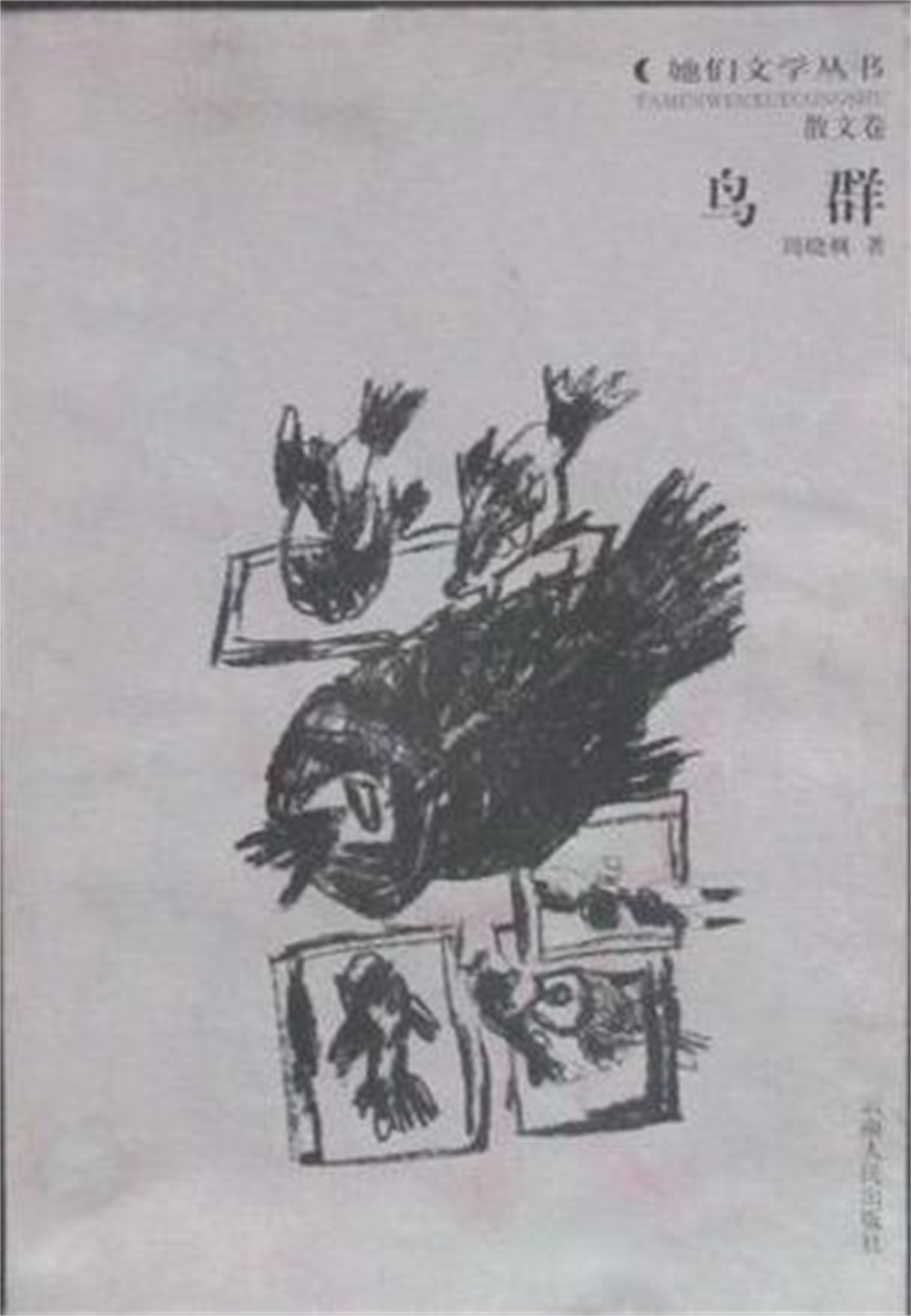
“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鸟儿已飞过”,读周晓枫的散文《鸟群》,我想起了泰戈尔《流萤集》中的诗句。鸟的一生美丽而高贵,飞翔是为了赶赴蓝天对它的邀请,它作为天空的使者,为大地和人类带来云端的讯息,羽翼所掠之处,是生命跳动的音符,是对自然呼吸的讴歌。
一
读周晓枫的散文,体会最深最强烈的,是其中鲜明的诗性品格。在《舞蹈与散步》中,这种品格被进行了一次高密度的展示。在作者眼里,“诗像口红,让嘴唇生动。像一只枕头,诗离黑暗中的梦想最近;诗像蛾子,与火焰保持危及生命的亲昵。诗像仙子跑丢的舞鞋,只是侥幸在人间被发现……”这只是一连串精彩的比喻开头,这种“诗性”在作品中还有许多,恕我从略。
我这般照抄原录,自然是出于喜爱,感至吟之咏之是一种享受,同时也是讨巧之举。既然只需简单列举原作,就足以使人感知其鲜明特色,又何必我来喋喋不休费力未必讨好?要了解一个作家作品的质地和色彩,最终应该去语言中寻找。
周晓枫散文中鲜明的诗歌烙印,使我们读到这样的宣言时备感会意——她说,“最纯粹的语言享受只有诗歌带给我,而不会是其他”。不妨说,收在这本名为《鸟群》集子中的几十篇散文,便是她这位诗歌的受益者,以散文方式的致礼。“我试图实现某些诗歌手法的介入,比如隐喻,比如变形,比如意义的纵深,希望自己的散文产生些许不同之处。瓦雷里说,散文是走路,诗歌是舞蹈。”闲庭信步品的是悠然自得,绰约舞蹈显的是欢畅淋漓。诗歌嵌入散文,诗性便融合为散文的灵魂,散文便成为诗歌的肉身。
应该说,这种愿望获得了丰硕的结果。诗性的感知和表达能力,在她那里,一定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上述那样的句子,在一般的文章中能找到几处就算不错了,在她那里却如乱花迷眼,其密度之高令人咂舌,躲都躲不开。文本是一片丰饶的原野,她大范围地收割佳句,以灵气的辞藻,布下华美的盛宴,只为一场语言的狂欢节。我们看到了一挂色彩斑斓的散文织锦,用诗歌的韵脚织绣而成,言有尽而意无限,回环流转、畅然不息。更为难得的是,最奇特的比喻,却以最自然的方式出现,机智、俏皮,如风行水上一样自然妥帖。作者自称是苦吟派,那么,这种毫无斧凿痕迹的呈现方式,巧夺天工,浑然天成,是对其功力的最好说明。
这种语言,以时而尖锐时而舒缓的方式,撞击着阅读者的语言触觉,潜移默化地摩挲着阅读者钝化已久的语感味蕾。唤醒其钝化已久的对于语言美的感受——不如说语言驱使人们进入存在的深处,那里,事物袒露着自己的本质,而平时它们是完全被遮蔽的。
你能想象出这样的句子么?“最小的水系在果实里流动,我把这个光亮的苹果举起来,就听到了声音,非常小的声音,类似于安静。”这是《种粒》的开头。“谁能感觉到衰老那吸盘般的力量?每时每刻我们向它靠拢……日月是光阴上的两条桨,划呀,送我到美丽广阔的地方。要像麦子,我从容不迫,着手安排自己安详的金色。”这是《存照》的结尾。这样的句子并非“众里寻他千百度”般寥若晨星,而是俯拾皆是,细腻掺杂着灵动,荡漾起文字的韵味,成为构成文本最主要的成分。这时候你会感到,它们映照出一个写作者的才华,就像指纹和生命的对应关系一样确切、不容置疑。然而,作者始终未曾忘记自己是驻足在散文的田亩之上,这种清醒的文体意识,或者说对散文的感受、表述方式的高度自觉,使得诗性因素最终被掌控在一个最适宜的范围内,一点也不喧宾夺主。
二
读她的散文,你能感觉到,即使在最纵情沉湎、兴奋迷醉的瞬间,理性仍然在睁着警觉的眼睛,监视着可能出现的忘形之举,并准备着随时予以制止。纷纭飞扬的感受,被理性整合驾驭,如同水流被纳入沟渠,其流动便有了方向,有了节制。又如同一只风筝,飞得再高再远,仍然被一根线牵拉着,这根线便是统驭整篇的主题、理念,或者用一个如今不大被提及的词语:中心思想。形散神不散,零星琐碎终是殊途同归。其结果,便是轻盈和坚实这两种不同的审美品格,很难得地统一于一体,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达到了一种堪称完美的和谐。这应该正是周晓枫散文独擅胜场的最主要的原因。
周晓枫作为语言杰出舞蹈者的表现固然让人难忘,但她的努力,绝不仅仅为了祭祀语言的图腾。在充满现代感的语言背后,折射出的却是纯正、明晰的精神理念,更多的是一种属于古典范畴的审美体验和价值取向。
《人们》从最基本的、因而也容易为人熟视无睹的生存场景中,撷取了一个个镜头,并生发出作者的感慨或憬悟。从指使孩子乞讨的母亲身上,她看到“我们习于讴歌的无私母爱在这里受到无情的玷污”。从街头小贩宽厚洪亮充满感染力的嗓音中——这样的声音应该属于歌唱家——她生发出关于命运、偶然的感悟:“种子未必能着陆于适宜的土壤,人一出生就可能存在着地域性的错误。”它们是深思的、悲悯的、超越的,总之,是浸润着人性的关怀的,是温暖如初春,是灿烂若朝霞,是荆棘丛中的一路生花,是沙漠中的一点绿芽。
作为一名热爱修辞的作家,是心之所向,是情不自禁,在这里,她同时又表现为一个深入的思考者,以优美的意境展现抽象的思想,以浪漫的情怀陷入清澈的沉思。
三
我想着重谈一下《鸟群》,即被用作书名的那篇数万字长篇散文。它以“五重奏”为副题,通过不同声部的变奏,完成了一个交响主题。同其他各篇相比,它更为朴素、简约、收敛、清晰、冷峻,能感觉到语言飞驰的欲望被作者加以有意的羁绊和压抑——然而这种压抑却在文本内部积聚起某种张力。鸟类成了她探测人性、展开思想、对生存发言表明态度的切入点和载体,成为人类观察自己的镜子。
她从太平鸟的尽职和欢聚,“看到世界对忠诚的公正报答”。从燕子为成为“空中王后”而付出重大牺牲,足部几乎完全萎缩,丧失了奔跑蹦跳的能力,“我看到了途中必然的苦痛与牺牲……牺牲是前提,是先决与必备条件——但正是在苦难里、在残酷中所展现的执着里,燕子体验着至深的生命狂喜”。她进而指出,这也是一切将创造视为生命意义之所在的科学家、艺术家的共同宿命。而从倍受人们宠爱的鸽子身上,她的发现更是堪称独特。鸽子既可以自由飞行,又可以随时回到主人的笼内,享用唾手可得的口粮。从鸽子的“具有投机色彩的双重身份”,作者感悟到世间“最名利双收的人是在天平两边找平衡的人”。鸟儿的习性再一次成为人类行为的旁证:“我们日益提炼出世俗生活的秘方:降低精神生活的高度,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匮乏。减少灵魂的成色,可以丰富肉体的娱乐……这就是生存可悲的等式。”但这并不表明她是赞同这种生存策略的,“鸽子的妥协与投降有悖于鸟的气节”,而她“多么震撼于那种对理想忘我的捍卫”。
这篇长文,让人联想到布封、法布尔、米什莱那些作家描写动物和昆虫的散文,但它的格局是不一样的,思维的疆域更为辽阔,也更为突出。
运城日报、运城晚报所有自采新闻(含图片)独家授权运城新闻网发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例:“运城新闻网-运城日报 ”。
凡本网未注明“发布者:运城新闻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