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运城晚报发布者:时间:2024-01-18
杨颖琦
1992年,苏童的代表作《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人们所熟知,那一年他26岁。2015年,苏童的长篇小说《黄雀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当时由孟繁华宣读的授奖词可以说是对苏童小说最为精辟的评定:“在《黄雀记》中,一切都遥望着丢失的魂魄。苏童回到已成为当代文学重要景观的香椿树街,以轻逸、飞翔的姿势带动沉重的土地与河流,意在言外、虚实相生,使得俗世中的缘与孽闪烁着灵异的、命运的光芒。三代人的命运构成了深微的精神镜像,在罪与罚、创伤与救赎的艰难境遇中,时代变迁下,人的灵魂状况被满怀悲悯和痛惜地剖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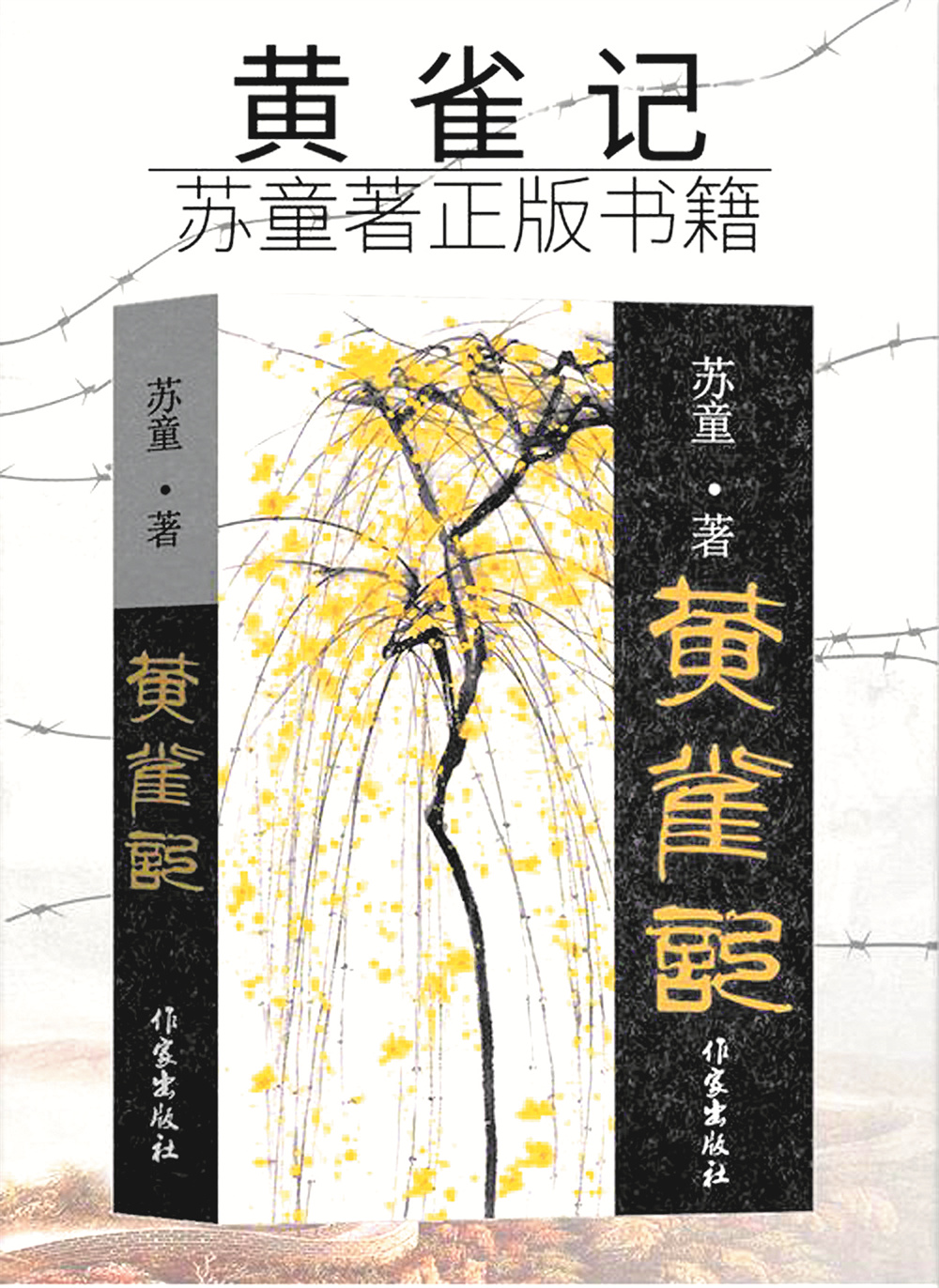
小说《黄雀记》始于祖父的丢魂,祖父掘地找魂的行为把他送入了井亭医院(精神病院),也让保润、柳生、仙女三人之间产生了宿命般的纠葛。全书共分三章:“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作者以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香椿树街”的一起强奸事件为背景,根据三位当事人的不同视角展开叙述,组成三段式的结构,在时代变迁中讲述三位少年的负罪成长和宿命般迷罪与罚的故事。书中写出了他们的成长与命运,以悲剧贯穿,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反映那个时代社会的变迁。
萨特在自己的独幕剧《禁闭》中借剧中人物之口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地狱,就是他人。”在《黄雀记》中三人的纠缠也构成了“他人即地狱”的关系模式。在这里人物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吃与被吃”角色的不断转换中上演着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一生被禁锢在香椿树街上,改变不了被他人干预的命运。丢魂的众人失去了自我意识,又受到他人对自我存在的干预。在这个故事里,他人既是黄雀,也是地狱。
萨特在著作《存在与虚无》的第三卷《为他》中对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问题进行了现象学的剖析。他将人的存在区分为“自为的存在”和“为他的存在”。自我首先是因他人而存在的。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关系因“羞耻”和“注视”建立起来。萨特认为,他人的出现和在场是自我意识产生的基础。他以钥匙孔的偷窥为例,为羞耻感来加以证明:当我独自一人时,我通过钥匙孔偷窥房屋内,我仅是对事物产生了意识,而没形成自我意识;但当有人走过来时,这会使我意识到有人可能在看我,这就产生了羞耻感。可见,通过他人目光的注视,我发现了我自己本身,同时,在自我意识中,我也发现了他人的存在。自我与他人建立起联系,在注视中产生“羞耻”的意识样式。
羞耻与喜怒哀乐一样,同为人类情感模式的一种。羞耻作为一种生发自内心的情感,只有在诉诸身体性表达时,才能被察觉。在这里,他人成为我存在的一个前提,不论是羞耻还是别的意识,正是因为他人的显现本身,“我”才能像一个对象本身对自己做出判断。在《黄雀记》中,香椿树街上的人们都在他人的注视中经历着羞耻。
在小说中,最典型的是保润与仙女的关系模式。仙女是保润羞耻的“他者”,仙女的无视蛮横始终是绑在保润身上的“绳索”。无论是他苦心经营的第一次“约会”还是多年以后向仙女“跳小拉”的讨债,都让保润在仙女面前无地自容。保润费尽心思准备了电影和滑冰之行,现实却让保润感到羞耻,“他好像一个宴会的主人,还没有举杯,便被宾客们驱逐了”。保润苦心经营的一点欢乐,在众人眼里成了笑话。当仙女恼怒地指责保润“头脑有病”时,众人用谴责的目光注视着保润时,保润的脆弱就这样暴露在他人目光之下,感到羞耻的保润只能选择“体面”地逃离。
而仙女所生的红脸婴儿作为两代生命的延续,似乎天生就处于“羞耻”之下。人们将婴儿称为“耻婴”,羞耻的耻,婴儿的婴。耻婴整天暴躁而绝望地恸哭,是为他自己,也是为香椿树街上的众人。
苏童把《黄雀记》的故事设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变动不安的时期。在香椿树街经历改革开放到新世纪的十余年间,物质条件迅速充裕,金钱和物欲大肆横流,大规模摩登事物迅速涌进人们的生活中,影响着世纪之交人的生存方式和人与世界的关系。时间在保润的身边流走,驻守井亭医院的他仿佛被时代抛下。当他被父亲替换回家时,家已经变得不再熟悉。祖父的房间似乎被某个“现代”怪兽一口吞噬,临街的窗户和墙体经过改装成为“花花绿绿的时装森林”。在“我”看来,“一个黑暗而衰败的世界被精心粉饰,旧貌换新颜,却是别人的世界了”。
尽管技术发展使人们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扩宽,但是人也在这种纷繁芜杂的可能性中越发清晰地认识到自我的他者性和不确定性,人们在过去和当下都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属。决定我存在的并非自身,而是世界的他者。这种宿命般的对自我的无力感与世纪之交的危机感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自我的流失,从而使“我”感到羞耻。
故事的最后,一切归于平静。故事中的三人都没能逃脱宿命的安排,死的死,离开的离开。而一直被宣布将死的祖父却留在了最后,抱着耻婴一起安静地看着这个新世界,迎接未知的未来。苏童以沉缓的语调诉说着香椿树街的故事,故事中,一切都“遥望着丢失的魂魄”,跨越了几代人,在这荒诞的画面中,饱含了人面对生存困境的无奈和无力。作者以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以文学的方式试图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危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只隐匿的黄雀,其实就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现实,这些人的命运。人生存在这个世界,暴露在世界他人的目光之下,无处可逃。
运城日报、运城晚报所有自采新闻(含图片)独家授权运城新闻网发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例:“运城新闻网-运城日报 ”。
凡本网未注明“发布者:运城新闻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